特朗普(川普)上任以来“退群”频频,按照中国媒体的标准,最近的“退群”愈发频繁了。
9月底,美国安全事务助理波顿(John R. Bolton,博尔顿)扬言,如果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ICC)敢调查“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行”,美国将制裁相关法官和检察官;10月3日,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宣布退出1955年《美伊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Amity, Economic Relations, and Consular Rights);10月4日,波顿又宣布退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Diplomatic Relations)的附属《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Optional Protocol Concerning the Compulsory Settlement of Disputes);10月13日,美国国务院宣布退出成立143年的万国邮联(Universal Postal Union);10月20日,特朗普在演讲中宣布美国将退出《中程导弹协议》(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一直指责特朗普“退群”成瘾。无疑,美国频繁“退群”严重冲击世界秩序,但仔细分析,特朗普此举是否真的离经叛道呢?又不尽然。
首先,很多被中国媒体标签为“退群”的行为根本不是“退群”。有的“退群”,其实美国根本没加入过,有的则根本不是一个“群”。
有的群,美国没加入过
前者的典型例子,就是中国媒体嘲弄美国“不接受国际刑事法庭管辖”。国际刑事法庭有时会和国际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ICJ)相混淆,其实国际刑事法庭只是一个在2002年7月1日才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成立的新组织,与1945年建立的ICJ没有任何关系。
关键是,在1998年制定《罗马规约》时,美国投了反对票。虽然克林顿政府后来在2000年12月31日又签署《罗马规约》,但并没有送给国会批准。小布什(小布希)上任后、《罗马规约》生效前,美国宣布不会加入这个条约,国务院(经手人就是波顿)向(将成立的)国际刑事法庭正式发信,书面通知了该决定,也表示美国将不会受《罗马规约》约束。虽然有人从美国宪法质疑总统是否有权力“取消签字”,但在国际法上不存在类似的问题。奥巴马(欧巴马)时期,美国一度表示愿意与ICC合作,但既没有重新签字,也没有送国会批准。
换言之,没有签字,没有批准,美国从未加入过这个组织,何来“退群”之有,更谈不上要遵守其约束。
其实,中国当年就有给ICC投下反对的“神圣一票”,中国也不承认该法院的管辖效力。2009年,ICC以苏丹总统巴希尔(Omar Bashir)在达尔富尔犯下“战争罪”为由,发出全球通缉令,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ICC的反对下仍接见到访的巴希尔,当时《环球时报》还发表社论《巴希尔被指战争罪,中国无义务理睬》。
双边条约不成“群”
美国退出的另一些条约则不是多边条约,而是双边条约,不是“群”。
最新退出的《中程导弹协议》就是一例。该协议是1987年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双边协议。苏联解体后,美俄继续承认条约的有效性,其义务没有扩展到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上。故自始至终,该条约都只是“双边”的。另外,美国在10月初退出的《美伊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也是一例。顾名思义,这本来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条约。
退出双边条约不是“退群”,这只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法理上不涉及“破坏国际秩序”的问题。那么,退出双边条约是多严重的事呢?事实上,类似事件比比皆是。在绝大部分双边条约中都存在条约有效期,大部分也有退出的程序。
比如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五条就规定:十年有效期,以及十年后可以提前一年通知的退出条款。2001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没有退出条款,但同样存在20年有效期。
因此,准确地说,“退出条约”符合国际法、国际准则和国际实践,它与没有经过合法程序的“废除条约”是两回事。但即便是报导“废除条约”,中国媒体双重标准也很严重。比如同是在二战中,纳粹德国废除《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中国称之为“撕毁条约”;苏联废除《日苏中立条约》进攻日本,中国则描述为“宣布无效”。以国际法眼光看来,这两个“废除条约”完全是一回事,都不合法。
《美伊友好条约》规定,退出的一方必须提前一年通知;《中程导弹协议》要求提前半年通知。美国都跟足程序了:它没有“非法”地废除条约,而是“合法”地退出条约,这不但符合国际法,也是国际实践中的普遍现象。

退出多边条约
美国也存在真正的“退群”行为,但深入分析之下彼此又有很大差异,其正当与否不能混为一谈。从国际法的角度,可分为三类不同的行为:退出政府意向、退出已经签订的多边条约、退出国际组织。
“退出政府意向”的例子就是川普第一天上任已经宣布退出的TPP。TPP在奥巴马时期签订,条约规定的生效方式是要足够数量参与国的国会通过方可,其标准是至少6个国家批准,以及批准国的GDP总和达到所有签字国的85%(Article 30.5)。而美国GDP的体量之大,以致如果美国不通过,TPP就无法生效。因此,TPP只是一个政府意向,尚未成为真正的协议,在这种情况下,退出合理与否固然可以争议,却难以作为指责美国违反国际法的理由。
退出已经签订的多边条约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分三个例子说明。
第一个是退出《巴黎气候协定》(Accord de Paris)。笔者一向反对美国退出这个条约,但这个协议本身就有退出的程序。
自本协定对一缔约方生效之日起三年后,该缔约方可随时向保存人发出书面通知退出本协定。任何此种退出应自保存人受到退出通知之日起一年期满时生效,或在退出通知中所述明的更后日期生效。
条约在2016年生效,于是美国虽然在2017年8月宣布退出,只能在2019年才能正式启动退出程序,再过一年才能生效。换句话说,美国现还在该协定中,受协定约束。2018年3月,美国通过的财政预算中,拨款1.40亿美元给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GEF),继续承担协定中的义务。这个数字只比前两年的数字低700万美元。美国国会还保证2019年拨款水平不会低于此。
第二个是退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附属《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注意,这不是退出公约本身,而是一个“任择性”(Optional)的文件。
巴勒斯坦指责美国把驻以色列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并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第三条第一款“使馆之职务如下:(a)在接受国中代表派遣国”告到IJC。它认为,“在接受国中”(in receiving State)意味著使馆必须在该国的领土上;它又根据联合国大会1947年181号决议,认为耶路撒冷应该是一个“由联合国监管的国际城市”。这个案件美国很容易赢:巴勒斯坦是否国际法庭认可的国家存疑;联合国安理会一系列决议都把大使馆所在的“西耶路撒冷”撇除出相关决议涉及的地理范围。这种情况下,美国选择退出《任择议定书》,是对国际多边体系的藐视。这是笔者不支持的,但同样不能视为违反国际法。因为《任择议定书》虽没有退出条款,但并不等于国家加入之后就不能退出,否则会导致很荒谬的结果。
一、条约如无关于其终止之规定,亦无关于废止或退出之规定,不得废止或退出,除非:(A)经确定当事国原意为容许有废止或退出之可能;或(B)由条约之性质可认为含有废止或退出之权利。二、当事国应将其依第一项废止或退出条约之意思至迟于十二个月以前通知之。
类似《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这种不需要负上特定义务的条约,属于退出最自由的一种,即属于以上的B项。从该附件名称中的“任择”(Optional)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美国退出甚至不需要提早12个月通知。
第三,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在笔者看来,在各种退群行动中,美国退出这份协议是最不具备国际法基础的。但也不排除美国可以用国内法的观点加以辩解。比如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协议不是“条约”,甚至算不上“行政命令”,只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政治性文件。美国也可用伊朗“违反协议”作为退出的理由。笔者认为,这些理由的正当性极具争议,即便能用美国国内法解释得通,在国际法上也面临不少困难,这毫无疑问损害美国的信誉和软实力。
从美国立国开始,美国政府签署条约,必须经过国会批准才能确认为法律意义上的“条约”,否则只是“政策”。一开始国际社会很不习惯这种作风,但久而久之,这也成了很多国家跟随的惯例。中国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现在还没有提交人大审批,因此至今不遵守公约,也是一个例子。
无论如何,对于退出多边条约而言,特朗普的做法不值得鼓励,但以国际法的目光,也不能说严重背离了国际实践。

退出国际组织
美国“退群”的第三种表现是退出国际组织。这里的例子包括: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退出万国邮联(三者都隶属联合国)等。当然,特朗普还曾威胁退出北约、退出世贸组织等。
在国际法来说,退出这些组织都没有问题。事实上,美国以前都曾退出(1984)又重新加入过教科文组织(2003);人权理事会在2006年取代人权委员会成立后,美国拒绝加入,2009年才改变主意。
特朗普退出这些组织的背后有两个关键字:一个是钱,一个是“话事权”。归根究柢,就是美国付出的代价能否与得到的权益相称的问题。
人权理事会与教科文组织的资金来源有两类:一是联合国的拨款,二是成员国的额外自愿捐献。在联合国拨款部分,美国一国就占其总经费的22%,中国则不到8%。在自愿额外捐献方面,美国更积极,如2017年,美国对人权理事会的捐献是2000万美元,中国捐款为10万美元。同理,对所有联合国组织来说,美国都是第一大的资金贡献者,可以说,没有美国的支持就运作艰难。
但在联合国“国与国之间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下,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只有一票。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美国拥有否决权,情况会好一些。但由于中俄也都有否决权,美国也无法顺利推进自己的议程。
在没有否决权的组织中,基于会员产生方式的配额、选举制度、及“一国一票”的投票制度,美国经常是吃亏的一方。
比如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是配额制,每个地区都有固定配额。其中欧美发达国家配额只有7席,比例不足15%。不少人权状况恶劣的国家都纷纷通过配额制加“选举”进入理事会。又由于没有“一票否决制”,人权恶劣的国家得以拉帮结派,把初衷为推广人权的组织,变为宣传“人权标准应因国而异”的组织,也成为反美和反以色列的工具(当然,以色列的人权状况也不见得好)。
这些机构改革困难,而且往往越改越糟糕。比如2006年从人权委员会改到人权理事会,西方发达国家的名额反而更少,这当然是因为改革也需要各国投票之故。
万国邮联
美国最近退出的万国邮联也是类似道理,虽然这不太涉及拨款的问题。其实,万国邮联是美国最早倡导成立的组织(1863年),对美国提升国际影响力有很强的历史象征意义,退出实属无奈之擧。
万国邮联和近年来很多国际组织一样都远离了公平公义的原则。在原先的《伯尔尼协议》中,为了公平起见,在假定两国之间邮出与邮入流量大致相同的前提下,规定寄件人只需买寄出国邮费即可。1965年,有国家抱怨,若两国之间一方寄出邮件的数量远远大于另一方,寄出邮件多的一方占便宜(因为获得邮费更多),原先处理就不公平了。于是又规定,各国有权收“终端费”(terminal due)以抵销差别,其初衷同样是为了“更公平”。
可是,这时万国邮联为了“公义”原则,决定把国家分出若干等级,富裕国家只能收低的终端费,贫穷国家可收取高的终端费,目的是帮助贫穷国家发展邮政。在制定等级时,中国还很贫穷,于是按发展中国家标准。这样中国寄到美国等国的邮件只收极低终端费,远不足以支付邮件到达美国后,美国邮政分捡送抵的费用,同时美国寄到中国却要收高终端费。
这本来是善意的初衷。问题是,万国邮联的等级划分几乎一成不变,完全与经济发展脱节。进入21世纪,两个变化令不公平的问题迅速严重。第一,中国经济增长极快,成为世界第二大国,物流业又极发达,根本没有“扶助发展”的必要,但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第二,邮递业务从传统的需求变成了跨国电子商务,中国商家利用低廉的运费,在网上购物中获得极大的竞争优势,变成电商之间的“不公平、不公义”的竞争。
它对美国的伤害是双重的:第一,美国邮政负担庞大的损失;第二,在美国电子商务市场的竞争中,帮助中国卖家赶尽杀绝美国卖家。换言之,美国邮政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补贴中国卖家,打趴美国卖家。
美国有两种办法。第一,可以在万国邮联提出修改动议。但万国邮联也是“一国一票”,在发展中国家众多的情况下,要通过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修改极为困难。此外,程序冗长;即便成功,改动幅度也只是聊胜于无,最后还得等几年的过渡期才能生效。第二,和中国签订双边协议,但2011年的双边协议同样糟糕,因为中国拿著万国邮联的协议作为谈判的基础和筹码,美国面临谈不拢就只能继续用万国邮联协议的困局。
可见,在万国邮联的限制下,除非像特朗普这样横下心来退出万国邮联,否则没有可能得到公平公义的结果。
世贸组织也是特朗普经常威胁退出的“群”,理由同上。2008年多哈会谈破裂后,规则修改完全停顿,美国也很难把中国剔出“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美国如果不发动贸易战,就只能退出世贸。

为了重新入群的退群
按照“退群”的目的,美国各类退群事件可以分为两类:政治目的、经济目的(也有兼而有之)。
因政治性目的所退的群,特朗普通常不打算重新加入。虽然他退群有很强的“回滚”奥巴马遗产的动机,但也要看到,类似的“退群”并无脱离传统共和党思维。
比如,美国以前曾退出过人权理事会与教科文组织。与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类似,小布什也退出过《京都气候议定书》(Kyoto Protocol);与退出《中程导弹协议》类似,小布什也退出过双边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2002)。共和党一向对伊朗核协议不满,换一个共和党总统,即便不直接退出,也必然用总统的权力“刁难”之而要求改变。
在经济性目的方面,虽然特朗普退群行动频繁,但与其说他是想真正退群,还不如说想通过威胁退群和直接退群获得更好的条件,有时甚至仅为了塑造其“守承诺”的形象。
比如特朗普在威胁退出北约时,不是为了退出北约,而是认为北约其它国家的军费开支不够,美国吃亏了。美国现在还想在中东组建“中东北约”,可见并非一味反对“群”。美国在退出TPP后,又放声可以考虑重新加入,不过要重新谈判。
从刚刚重新签订的《美墨加协议》(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USMCA)则可以看出,特朗普的要价也不是那么高。媒体把USMCA视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的升级版:因为除了奶业与汽车业的小幅改进外,两者的实质差别实在不大;更早前签订的《美韩贸易协议》同样也只有小幅的改动。
特朗普主张“美国主权”,反多边主义,尤其是反对多边主义中的仲裁制度。但从USMCA看,特朗普也不一味抗拒国际仲裁:在加拿大的坚持下,仲裁制度仍然保留下来了。由此可见,在经济性的议题上,川普退出的多是实质性的义务,反对国际仲裁不无妥协的空间,底线不是那么高不可攀。
但在政治问题上则相反,特朗普坚决反对仲裁制度,却不太反对实质性义务。比如在退出《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的时候,美国强调会继续遵守《维也纳外交问题公约》,只是不再承担解决争端的程序而已。这其实也和共和党的态度没多大差别: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共和党的里根总统签字,却没有提交国会批准。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共和党议员反对当中的仲裁方式。此后美国不断宣称自己将主动遵守海洋法公约,但不承担被仲裁的义务。
否定之否定般的演变?
现在的国际格局的变化,也是特朗普在“退群”问题上,不得不走得更远的原因。
全球化不是新鲜事。一般认为1492年是全球化的开始。最近20多年,全球史兴起,历史学家更倾向把全球化的开端往前推。但我们现在一般讨论的“全球化”,是一套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下的“全球化” ,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全球协作化,带有强烈“协作”意味的多边主义体系,即“建群”,正是这套话语的关键。
如果以此为标准,“全球化”其实并没有很久的历史。美国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提出国际联盟的构想不过是1910年代的事;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提出成立联合国不过是1940年代的事;各类“泛”组织,包括北约、欧盟(及前身欧洲共同体)、东盟等都不过二战后才出现;经济的“全球化”,如果以WTO签订为标志,更只有短短二十多年。
从国联到联合国再到世贸,这套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体系都是美国一手主导打造的,威尔逊、罗斯福等人这么做更多是出于理想。此外,国际关系学者也早有论证,多边体系对头号大国有好处。比较多边体系和双边体系:双边体系单向地有利大国控制小国(通过谈判实力不平衡);在多边体系中,大国和小国、大国和大国之间也能互相约束。多边体系对小国是最有利的,像美国这样的最强国来说,固然会被规则所束缚,但若能主导制定规则打造多边体系,是建立一个“全球秩序”的最好工具;对于有志逐鹿天下的次等强国,多边体系却是约束成分更多。因此,如果要打造“全球秩序”,多边体系依然对美国最有利。
美国共和党人虽然一般没有那么强烈的“全球秩序”情结,但“山巅之城”的模范情结不比民主党小。“多边体系”对他们来说,是“拉帮结派‘对抗’敌人”的工具,而非把“敌人”也拉进来,限制“敌人”的工具。
很多人认为特朗普“退群”是倒退,即使它不能被回滚,放在更长的历史角度中,也未必不是“否定之否定”式的演变的必经阶段。
在“退群”上,特朗普比其他共和党总统叫得更大声,令人认为他在“退群”上走得更远。这与特朗普的个人性格和理念有关,特朗普喜欢高调,强调“美国优先”,否认共同价值与共同利益,也对打造新的全球秩序毫无兴趣,“山巅之城”情结欠奉,道德形象对他来说也重要。很自然,“多边体系”对他来说更远不如双边体系了;“退群”也更没有顾忌。
尽管如此,以上例子均说明,特朗普所退的“群”,以前的共和党总统大多都做过。因此,过于强调特朗普的“退群”的严重性和独特性,也是错误的。以上例子同样说明,现在的国际格局的变化,也是特朗普在“退群”问题上,不得不走得更远的原因。比如,最新退出的《中程导弹协议》(尽管不是退群),美国的论点之一,同样也因为协议没有把中国也包括进去,已经不合时宜。
回过头看,特朗普走得并非这么远。它没有破坏国际法,没有破坏国际交往准则。它代表一种新的潮流,但未必到了难以回滚的程度。再说远些,“全球化”到底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还是只是一个周期的一部分,其实谁也无法下定论。很多人认为特朗普“退群”是倒退,即使它不能被回滚,放在更长的历史角度中,也未必不是“否定之否定”式的演变的必经阶段。
(黎蜗藤,旅美历史学者,哲学博士,关注美国政治、领土领海争议、东海与南海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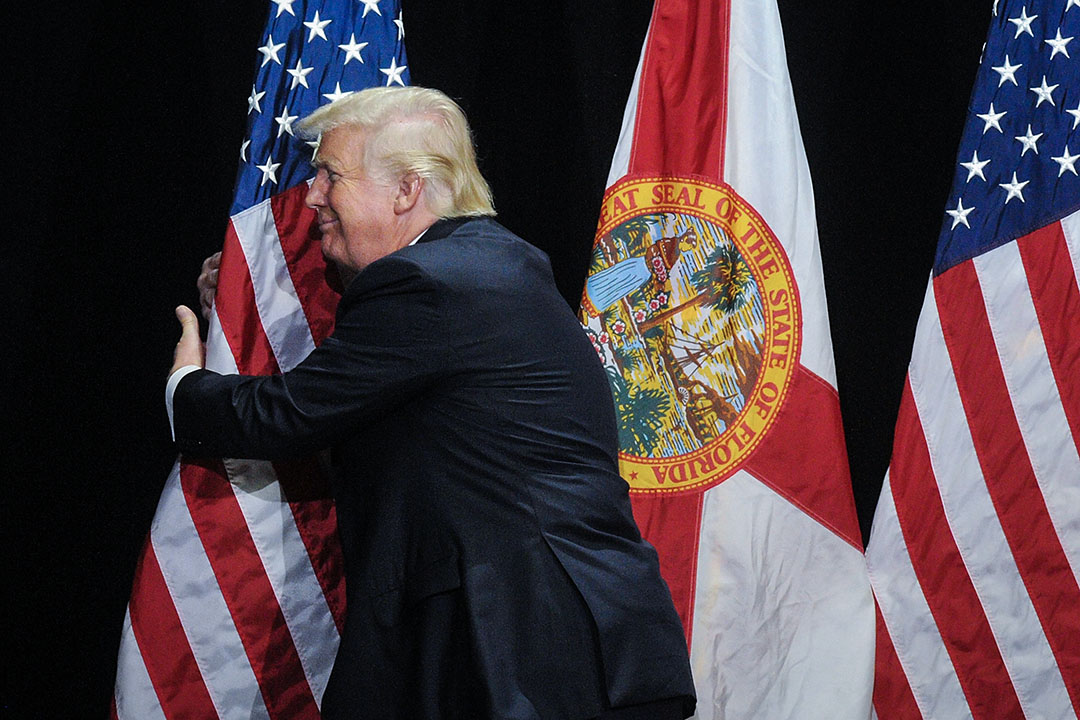

我觉得这篇文章就是说明了一个道理: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一个世界。从古到今,从动物到人类,一直没变过
其实也就是美国回到了冷战时期的样子
所以想问,退群这个不怎么稀奇完全可以不大张旗鼓的事情,现在似乎被自豪地表现为政绩之一,其目的何在?似乎给国内反对派把柄,和国际社会批判其信用与责任的一大利器。
贊同作者的觀點和分析框架,但是有些具體的國際法問題則分析得不夠準確和深刻。比如巴勒斯坦訴美國案的分析停留於「能否退出」,沒有點出巴勒斯坦本次訴訟的本質目的;倒數第二個小標題下的「仲裁」應為「(強制)爭端解決制度」,這是國際法術語的不嚴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