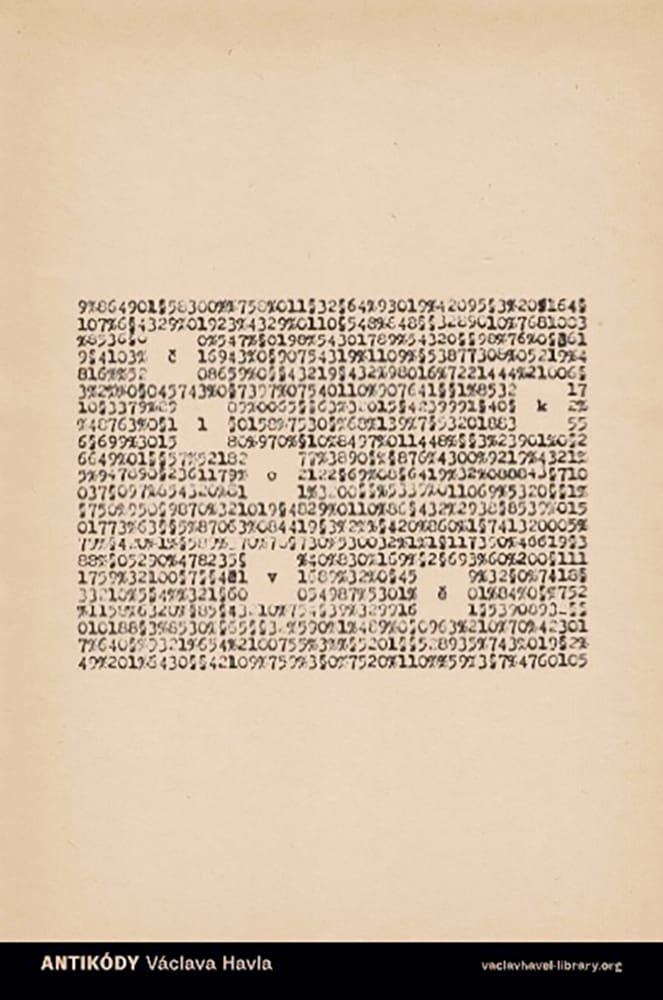看了我的文章比較久的讀者,應該記得我在五年前寫的「這時代的愛與希望」系列。首先我當時果然還是年紀小(畫外音:沒有多小),居然給系列改了這麼一個日本熱血動漫的名字,但那時候我讀了許多共產波蘭和捷克的抗爭史,加上香港發生的一切,本就莫名容易感動,加上評論編輯雨欣不時冒出來說「來一篇」的約稿神技,所以就有了這個系列,也有了這個名字。
可能有人說整個系列的軸心就是拒絕集體主義,但我會說那只是一個「順便」的事情;我想說的還是人如何能對自己的生命負責。哈維爾批評西方將捷克和蘇聯內部抗爭者臉譜化,以為他們都是反共產反極權的「民主鬥士」,但其實「異見者」「不過是在實踐生命的時候無可避免地跟權力槓上的人而已。他們是醫生﹑社會學家﹑音樂家﹑作家——各行各業的普通人。」人的獨特性是對抗謊言和集體主義的根本(不贅,大家有興趣可以重讀,看看五年後這幾篇文章還有沒有長尾,或者我還可以寫個續篇)。
哈維爾連各種「主義」都不愛講,覺得死板的「主義」困住了活生生的人,更不可能愛講星座,如果讓他知道有MBTI(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可能會氣得在土裡翻身。70億人70億種生活,怎可能硬生生分成16種?我其實也是這麼想的,但無奈MBTI話題實在鋪天蓋地,不止在Threads和Instagram上有大量MBTI內容,如果你近年有去過韓國的話,你會發現街上有各種MBTI戀愛﹑職業﹑理財諮詢,MBTI儼然全面取代了此前的星座,成為了(好像沒那麼神秘)的人類分類學。韓國有個關於「T人」(即傾向理性的人)的段子,是說如果朋友跟你說「今天很不開心,所以我去買了個麵包」,然後T人就會問「買了甚麼麵包」,而不是問朋友為甚麼感到不快,所以T人就是個沒有感情的人。但其實會這麼問根本和T人不T人無關,基本就是個不會和人相處的爛朋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