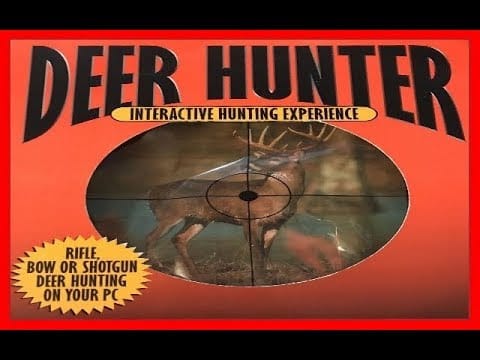2001年,我来香港开会。会上有很多有趣的人,我记得和一个中国女学者茶歇时闲谈,她问我业余时间有什么爱好,我说美国的博士项目都很紧张,业余时间不多,但我都会在寒假抽时间去森林里打猎。我顺口问她中国人是不是也喜欢打猎,这问题不知为什么让她觉得受到了侮辱:“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需要食物都会去商店里买,我们不需要狩猎为生!”我赶忙解释并无恶意,但于事无补。我好奇难道她以为我是因为饥饿才去打猎吗?后来,随着我对中国了解的深入,我发现在这个国家,生活中你的职业离动物距离越近,人们就越会认为你很穷。还记得我的学生在电影课作业描述《断背山》的两个主角时,称他们是家徒四壁的穷人,其实在电影里,这两个角色都有房产和货车。但因为他们的生活离动物太近了,大家就联想到他们很穷。学生还写这两个人物缺乏“野心”、“没有职业规划”,所以“只能放羊”,并怒其不争地指出两人“学生时代应该更加努力才是。”
离开美国的二十年里,我逐渐意识到打猎在地球这个角落是件稀罕事儿。每次我在香港看到白色的野猪,视线就会本能得绕到它的肩膀之后——如果要开抢杀它,那是落点所在。当然我没有枪,有了也不能在香港射杀动物,所以我这些年都是在电子游戏里过瘾。
似乎大家对爱好打猎的美国人有这样的想像:红脖,醉鬼,拎着AR-15见到什么就射什么,座驾一定是皮卡。那我显然不符合这样的想像,我没有皮卡,不喝酒三十年了,还不小心读了个博士。但事实上,我认识的猎人中也没有一个人符合上述想像——不是说猎人不喝酒,但真正的猎人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不会把酒精和武器混在一起。我第一次打猎是在新英格兰猎鹿。新英格兰的鹿比起美国其他地方并不算多,郊野空间也不算大。很多当地人与其说是打猎,不如说是找个借口在郊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那次我只看到两头鹿,还一个都没打到。要说猎物丰盛的地区,是后来我在华盛顿读书那阵,总去马里兰打猎,那边雪少,蚊子多,但是鹿也真是多,常常满载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