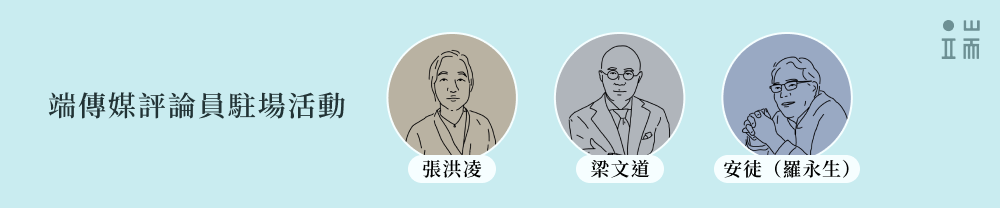三年前我做过一个尝试用ChatGPT取代同事的实验(现在想起来,我到底有多邪恶),那次好像是第一次和评论编辑雨欣聊“评论”这回事。那时她尝试用ChatGPT代替我写“这时代的爱与希望”评论系列,发现AI取代不了我(当然)。她当时说,一篇好的评论不外乎三方面:
第一是问题意识:大家看到的事实都一样,但要在矛盾和落差中敏锐发问,并有自己的框架和结构。
然后就是作者性,即是对问题的独特论述过程。论述过程可能包括作者自己的研究﹑专业领域的知识和经历。然后作者要有和他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才是能够成立的评论。
最后是文笔,但不是要雕花,重点是不仅仅让读者看到作者自己,也看到与其他人交流、沟通的意愿,并传达到。
听起来蛮难的,还好我在她眼中还算是个好的评论作者(不脱稿的时候)。因为要推出驻场评论人计划,我特意去研究了一下评论这种技艺的历史。现在评论常被新闻编辑室收编,但其实评论作为一种文体,历史可能比报业﹑新闻还长。最早期的“评论”,可能是我们在古书里会见到的注﹑疏:例如中国的春秋三传(“春秋笔法”的由来)﹑犹太经典《塔木德》正文旁的拉比论战﹑《圣经》的各种释经(exegesis)。到了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把 doxa(看法)跟 phronesis(实践智慧)分开,后来也有了西塞罗(Cicero)这种教人如何公开说服人(或吵架)的评论家;中国则出了“太史公”司马迁这种把历史变成对权力、命运、制度的道德审判的评论家。
到了19世纪,评论随印刷术兴起完全进入公共事务范围,甚至我们可以说近代新闻史本身,就是被几篇“重磅评论”模塑的。1898年,法国作家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s)后以头版大字发表著名的《我控诉》(J'accuse...!),直接点名挑战军方、司法、政府。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10个月,作家 Henry Luce在《LIFE》杂志刊出6千多字长文《美国世纪》,直指当时仍置身二战事外的美国对塑造世界秩序有历史责任,预言了战后美国的自我理解。上世纪美国第一健笔 Joan Didion一句话刺穿60年代看似开放﹑进步,实质虚无而苍白的时代布幕:“很多人相信六十年代在1969年8月9日戛然而止。”那天邪教领袖曼森的追随者闯入洛杉矶一栋豪宅,无动机残忍杀害五人。在众声喧哗中,Didion 直面时代:六十年代我们相信爱与和平会带来善,但一切“解放”的口号,最后却导向了毫无意义、纯粹暴力的杀戮。
在半世纪后投入新闻行业的我们常想,今时今日的评论还可以做成甚么样子。都说我们活在新闻“deskilling”的年代,三年前我做那个ChatGPT实验时,似乎就是公众的AI焦虑元年,“取代”叙事开始铺天盖地,新闻记者与写作人,多少都有种“亡国感”。当时我们说,这个随口就能吐出万字的工具没法取代评论作者,起码没法取代“好”的评论作者,但“好”的界线会不会随著劣币驱逐良币慢慢改变?2024年底,有研究指出网上由AI生成的文章,数量已经多于非AI生成的文章。在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意见的年代,评论人还有公共责任吗?在威权社会不断扩张时,我们还能像左拉一样高呼“我控诉!”吗?还有没有评论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是谁,身处在哪个历史节点,应该如何理解自己﹑时代﹑还有历史与道德责任?
我们是带著这些疑问来策划端的驻场评论人计划的。我们邀请了三位在不同领域已经有极高成就的评论人,来陪我们做一次好玩的实验:我们想知道,对一件事的深入思考﹑拷问可以去到甚么程度,能逼我们问出甚么更深层,更让我们不敢直视的问题。我们也想知道,“常识”(common sense)或知识在资讯爆炸但注意力太少的年代,还能不能在公共讨论中有一席之地。前几天,audience同事们发放了这三位评论人的“标签”和剪影,让读者竞猜驻场评论人的身份。相信答案呼之欲出,但今天终于可以正式公布(点击名字可以收藏他们的作者页!):
- 梁文道:我们这一代的知识青年(包括我自己)肯定都受道长影响甚深。2009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他写了“我们守护记忆,直到最后一人”,而这句在每年春夏之交依然在我耳边回响。同年他出版了关于爱情的散文集《我执》,我至今仍能随口引用里面的句子(很明显,2009年的我也比较关注爱情这回事):“等待这种东西并不如我们所想,一定要有目的,一定要有等到的那一天。这种植物执迷不悟地生长,等待就是它本身的目的。不一定等到什么,只要等,联系就在。”多年笔耕不懈的道长会在驻场计划中,和读者分享“常识”是甚么,公共讨论之不能及可能,以及回答我们许多人在这个纷乱时代的诘问:文字还有用吗?
- 张洪凌:洪凌老师是驻美的双语作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者门罗(Alice Munro)的译者。她写的异乡人至今仍是我在端最爱的文章之一,我常常想起她笔下那些仍紧紧系住后来人的,历史的幽微线索。某年春节我推荐了这篇文章,那时我是这么写的:“这篇文章想讲的,大概不止古典文学里常见的‘乡愁’。它在讲的是一种我们即使没有经验过,但依然不能避免地共同承担的历史创伤--因为那些未解的﹑暴力的过去,像幽灵一样以某种形式“徘徊”到现在。”洪凌老师不久前与文中的柬埔寨老板夫妇重新联系上,并随他们踏上了归国的旅途,并会在驻场评论系列中,与我们分享她在旅途中对殖民﹑历史与创伤记忆的更多思考。
- 罗永生(安徒):许多香港人和我一样,是从生哥那里学习“知识分子”应该是怎么样的。他的评论不只是对当下的锐利洞察,更是一种道德姿态的示范:始终坚守理性的底线,却不失去对具体人生的温暖关怀。他写过无数篇关于香港身份与殖民遗绪的文章,但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看似谈论历史或理论的文章背后,都藏著对普通人生活经验的凝视。生哥会在驻场系列中,细致地拆解香港文化精神内部的撕裂、留港者与流亡者之间微妙的权力不对等,并在“跨国主义”与“流亡政治”的交汇口,提出更清晰的伦理追问,帮助我们理解:在这个香港分裂与重组的时代,评论的责任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也刊出了生哥的第一篇文章:跨国还是流亡:拉扯中的香港精神。
端传媒评论员驻场活动现已登场!这次活动邀请了三位评论人,他们会在端发表一系列评论文章,同时与读者互动。现在注册成为会员,即可领取电子报,率先接收最新评论文章推送。
除了能读到三位评论人的驻场系列,读者还有机会在端闻听到他们和端编辑团队的对谈,以及在线上小聚与他们直接对话,听他们如何思考当下的关键议题。三位评论人也将在评论区与读者进行AMA(Ask-me-anything)互动,打破评论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同时,他们的推荐书单、文章清单等延伸内容,将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地图,让这三个月的驻场成为一次深度的思想对话,而不只是单向的评论输出。
在此,我邀请每个还相信文字﹑知识与思辨的读者参与我们在2026年的第一场新闻实验。时局纷乱,也许你也有过觉得“算了吧,世界也不过如此”的时候。我想请你跟我一样,尝试直面而不是逃避时代的沉疴:只因未来的可能性,往往蕴藏在我们今日的选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