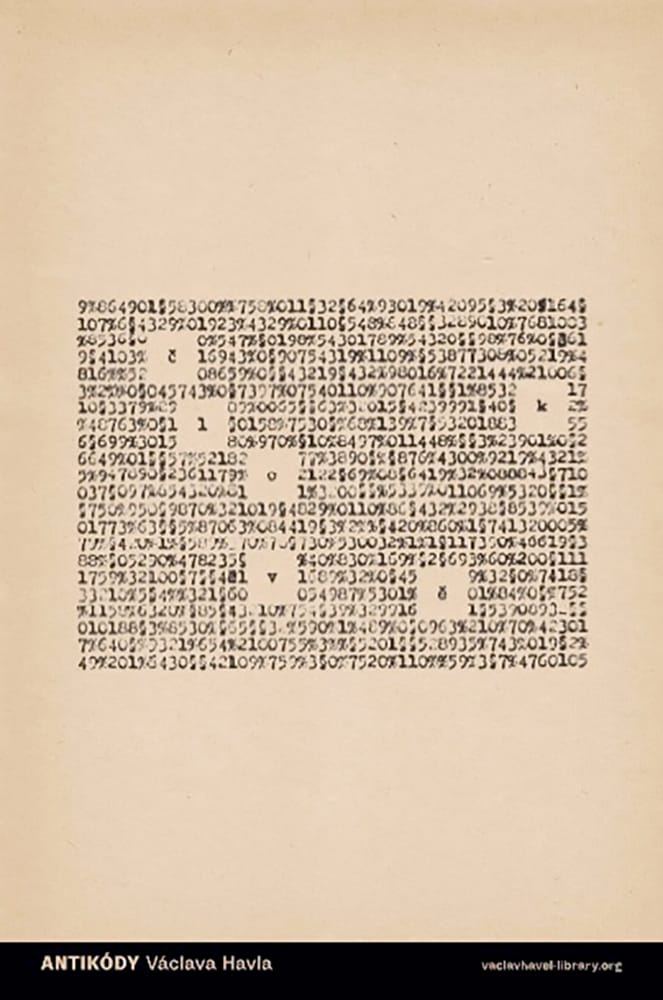看了我的文章比较久的读者,应该记得我在五年前写的“这时代的爱与希望”系列。首先我当时果然还是年纪小(画外音:没有多小),居然给系列改了这么一个日本热血动漫的名字,但那时候我读了许多共产波兰和捷克的抗争史,加上香港发生的一切,本就莫名容易感动,加上评论编辑雨欣不时冒出来说“来一篇”的约稿神技,所以就有了这个系列,也有了这个名字。
可能有人说整个系列的轴心就是拒绝集体主义,但我会说那只是一个“顺便”的事情;我想说的还是人如何能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哈维尔批评西方将捷克和苏联内部抗争者脸谱化,以为他们都是反共产反极权的“民主斗士”,但其实“异见者”“不过是在实践生命的时候无可避免地跟权力杠上的人而已。他们是医生﹑社会学家﹑音乐家﹑作家——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人的独特性是对抗谎言和集体主义的根本(不赘,大家有兴趣可以重读,看看五年后这几篇文章还有没有长尾,或者我还可以写个续篇)。
哈维尔连各种“主义”都不爱讲,觉得死板的“主义”困住了活生生的人,更不可能爱讲星座,如果让他知道有MBTI(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可能会气得在土里翻身。70亿人70亿种生活,怎可能硬生生分成16种?我其实也是这么想的,但无奈MBTI话题实在铺天盖地,不止在Threads和Instagram上有大量MBTI内容,如果你近年有去过韩国的话,你会发现街上有各种MBTI恋爱﹑职业﹑理财咨询,MBTI俨然全面取代了此前的星座,成为了(好像没那么神秘)的人类分类学。韩国有个关于“T人”(即倾向理性的人)的段子,是说如果朋友跟你说“今天很不开心,所以我去买了个面包”,然后T人就会问“买了甚么面包”,而不是问朋友为甚么感到不快,所以T人就是个没有感情的人。但其实会这么问根本和T人不T人无关,基本就是个不会和人相处的烂朋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