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墨西哥格雷罗州(Guerrero),位于墨西哥西部。2014年9月26日,43名师范学生参与一场抗议行动后在这里被警察拘捕后,被转交黑帮,最后被虐待、烧死及埋在中山,后激发了据说是墨西哥五十多年来最大的一埸社会运动。2014年11月26日,一百万墨西哥人民走在首都墨西哥城的改革大道上,要求政府彻查事件及反对政府以反毒品战争打压和杀害社运活跃分子。
旅舍的人告知那是危险地,在墨城中的“革命左翼”亦劝说危险勿近,但我遇上这名原籍格雷罗州在西雅图长大的瘦小女性主义艺术家,她说一个人在这片土地上走了多年,她并不认为像人们说的那样,她的描述中透着她对那片土地的复杂情绪。然后我就跟着她,来到她格雷罗州某小镇上的老家──一片人民武装自治的丛林……

辞掉香港的工作,到达墨西哥已经两个月,因学习西文及一点小意外,一直滞留墨西哥城。收拾好行装准备西进会合友人,在出发前一天才收到信息得知会合安排,正担心大背包过重无法徙步进 Jungle,友人说她父亲会开车载我们进丛林。在石屎森林住惯了的我,脑海里一直幻想的是深山大林,不走上数小时不能称之为 Jungle,一下子不知自己将要去的地方究竟何模样。
摇摇晃晃向丛林进发
我在距离墨西哥城十小时车程的 Zihuatanejo 会合友人,这个曾经只充许女性到来祈祷的地方,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被开发成旅游胜地的小城,位于太平泮东海岸墨西哥的西部,是友人的出生地,“Zihua”就是女性的意思,这是女性之城。
在此转乘半小时巴士到达名叫 Petatlan 的小镇,然后由友人六十八岁的父亲驱车载我们到深入山丛中他们的家。由混凝土大路开进土泥小路,摇摇晃晃的向丛林进发,友人告知我们已进入一个外人不被充许的自治区,这里没有政府、没有警察、没有军队,但有农民自组的“警察”(自愿性的武装)监察进出丛林的人及保护社区。
这里的人民反抗,守护自己的土地。
我惊讶,立时转向车窗外尝试搜寻守卫的武装人民,车外是正值干旱期的小山丘,道路两边除了半绿的矮树,还有简陃的围栏围着的已收割完的粟米园,树丛短矮,疏疏落落,有点像中国南方的山头,但较为干燥。友人说,雨季时雨下得励害,树丛深绿一片,满山开满花。
以游客的角度来看,这丛林并不是足以长途跋涉到访的惊艳之地,就是一片片小丘陵。我遍寻不见守卫的人民警察的踪迹,友人说,他们有自己的方法,车子刚拐进他们就会察觉,如遇陌生人或车,即以 walkie talkie 通知整个社区,如没有人回应认识来客,将会即时有人拦阻,妇女小孩也一起出动,把人赶离丛林。不像浪漫而神秘的 Zapatista,他们不蒙面也不穿军装也不骑着马而来,他们就是一副农民装束。
她的家族史,自一百年前墨西哥革命起,是一个关于原住民解放和抗争的故事。
20年前,在忍受了二十多年军管,大量该区抗争的原住民被谋杀及失踪后,这片丛林的人民𢹂老扶幼,占领了警察局,没收了武器,把警察、军队及为政府和为毒贩黑帮办事的人都赶出丛林,建立了这个自治区。友人说,这就是外人认为这里“危险”的原因,因为这里的人民反抗,守护自己的土地。自治后,外人只能经由由社区的成员介绍和带领才可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友人说丛林属于任何人,原住民在丛林之中不断地迁移,不同季节不同年份,因着耕作、放牧或狩猎的需要而迁徒。她的先辈数百年来一直如此,直到政府来收他们的土地。
这里没有 Zapatista 的名气,没有世界各地来朝圣激进朋友,安安静静地,她/他们的故事在延续,正如发生在友人家人的故事。她的家族史,自一百年前墨西哥革命起,是一个关于原住民解放和抗争的故事,同时亦关于在男权主导社会之下,那些在战门前线的女战士们,为土地为她们家人为她们的人民流血牺牲,从未被正式写进历史的故事。他们叫那些抗争的人民 Guerrero Fighter,格雷罗战士。
在这里,我避世了五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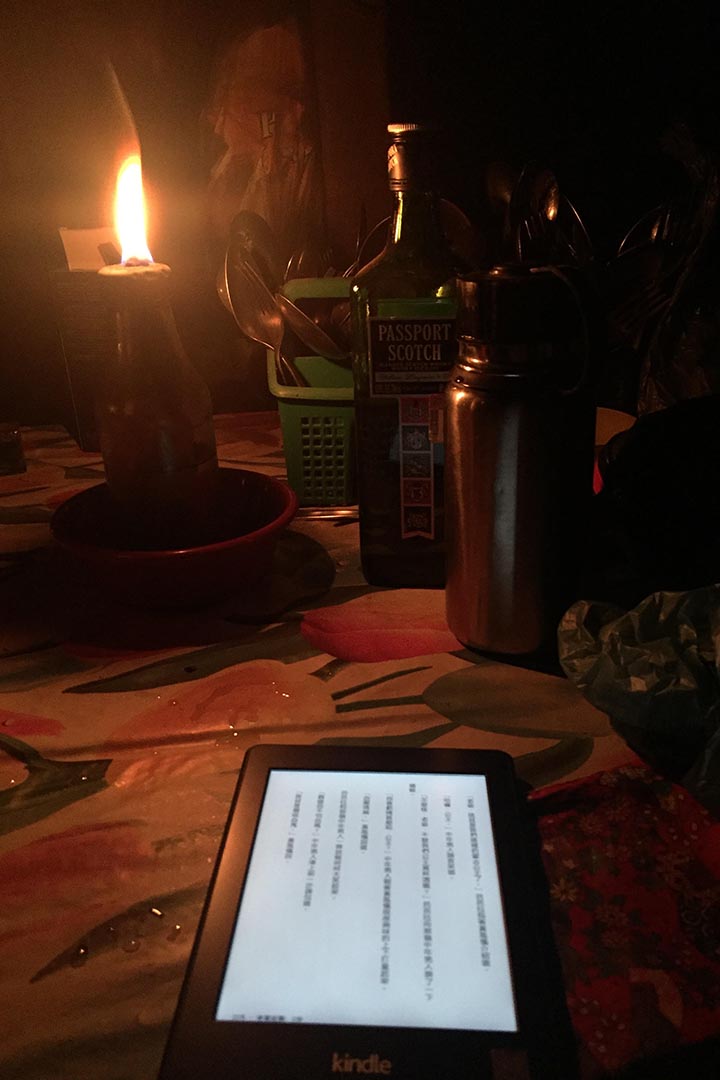
这五天伴着我的是:
-没有网络没有电视没有新闻
-两间木屋和一间正在建设中的大石屋
-九只不同品种的狗只及五只刚出生两周的小狗(其中一只在我离开前一天死了)
-一大群公鸡、母鸡和两群刚出生不久的小鸡
-一只刚生了一窦猪仔但不肯喂奶的黑猪和另一只刚生了一窦猪仔要同时承继那不肯喂奶的黑猪的猪仔的黑猪
-一雌一雄两只孔雀
-三百只各有名字的牛(但我见过面的十只手指数得出,据说牠们漫山遍野走,好夜都唔会回牛栏)
这五天我做了以下的事:
-每晚七时后挑灯(火水灯)夜读或夜聊然后九时进睡
-每早三时至五时不等被鸡、狗、猪轮番吵醒(牠们喜欢凌晨对山歌)
-然后由六十多岁的友人母亲煮早餐喂养
-看友人父母忙喂养家畜及修建新房子
-在树荫下的吊床看书睡午觉或逗逗小狗或追着孔雀拍拍照
-在日落西山前在房子周围稍作游览
-跟着友人及其父母到小镇购物,听他们一路与邻居聊天,及看一路坐顺风车的邻居上上落落
-跟友人随意采路边的芒果然后第二天告诉邻居:我们采了你的芒果
-跟友人串门子食晚饭听着妇女男人小孩一堆各聊各然后大家拿出粉红女性情趣内裤笑谈一番
这样宁静而简朴的生活,是友人一家,及丛林里的原住民,以近百年的血泪来保护和维持的。
盖自己的房子,养300只牛,种28种粟米

二十五年前,友人五岁那年,为躲避政府军队的杀害,她父母带着十一个孩子逃到美国。自小,友人被父母告知自己的国家在战争中。她母亲亲眼看着亲人被杀,好几名兄弟及其家人被杀或被失踪。十五年前,在人民把政府、军队和毒贩赶出丛林后,友人父母才摆脱恐惧,重回老家。五年前两老退休,决定回来丛林重建家园。
他们一家拥有的丛林占据了一整座山头,房子设在山谷。两老以六十多的高龄,加上一名儿子,他们养三百只牛,还有鸡、猪、牛、狗一大群,种了一大片粟米、香蕉及木瓜。三百只牛都有名字,据说友人父亲和哥哥认得出不同牛的样子,牛漫山遍野走,夜来也不回家,他们也不怕。据说有一只老牛,是她外婆的宝贝,是她的第一只牛,经常数月也不回来,病了就回来要人照顾,大家不愿意卖掉牠,留着纪念她外婆。
他们说以现时的时势,经济危机及粮食安全谁也说不准,这片自给自足的丛林将是他们一家人最后的保障。
他们到处收集不同品种的粟米和香蕉,据说有二十八种粟米及十四种香蕉。他们有女儿十二名,其中一个小时候已夭折,十一名儿女各自用自己的方法贡献,打算以两年时间把新房子建好。房子的设计由当建槃师的哥哥负责,堂兄负责监工,另一做地盘工人的哥哥教工人本地取材造砖头,地基的石头就在山上找,母亲负责园林种花种草,父亲精于山涧及地下水流,设计以天然的方法储水,并沿水流种植以过滤净水。他们说以现时的时势,经济危机及粮食安全谁也说不准,这片自给自足的丛林将是他们一家人最后的保障,同时也延续他们家族在丛林的历史,他们是家族中仍生还的唯一回到这片山头重建家园的。
向山上走十分钟便是他们的老房子,用古老的方法建成,以木头为框,批上黄泥浆,已倒掉多年,见证她们家族的历史。二十多年前,据说这个山头住了十几户人家,全是她祖母的儿女及家室。现在被杀的、被失踪的及走难离开的,山头已冷清。
必要时,男女老幼都是土地捍卫者
一百年前,友人的曾外祖婆,是墨西哥革命的女战士,拿枪上战场,她的革命血统留给了女儿。上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友人的外祖母是土地自由运动(lang right movement)的核心,带领原住民妇女建立咖啡集体农场,占领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反抗政府及军队反对土地私有化,祖父亦是积极参与抗争的斗士,最后整个家庭被军队针对,几个儿子及其家人被杀害及无故失踪。外祖母逃到 Acapulco,一个位于格雷罗州较南的海港城市,并参与土地占领运动反对出售土地给跨国酒店财团,祖父逃到南部另一个州 Chiapas。他们一面躲藏,同时继续参与原住民土地自由权利斗争,十年后他们在墨城重聚,再参与墨城的占屋运动,一生到死,即使家人在眼前被杀害,友人祖父母没有动摇过捍卫他们在那片丛林生存和生活的权利。他们没有读过书,但受过墨西哥反殖民革命的洗礼,在生活中深刻认知到土地的重要性,及资本主义发展将会如何剥夺原住民的生活权利。
这些“战士”,只是在这片土地上,种粟米火芒果香蕉,养牛养鸡养猪的原住民,男或女,老或幼都要在必要时成为捍卫者。
对原住民的这波残杀,自四十年前军管开始,在以维持社会稳定为由夺取原住民土地为实的军管之下,被暗杀和被失踪的人不计其数。友人堂兄,老幼一家,一夜失踪,廿多年来都没有消息。自2014年43名学生被警察移交黑帮并烧死埋葬的事件爆光后,有原住民自组调查队,在格雷罗州挖出多个乱葬岗,几百具无名尸体,43名学生不是起点,也并未是终点。他们说现任总统及其政党是为毒贩做事的,但打着反毒(WAR ON DRUG)的名义十年,大量杀害反抗的原住民及社运分子。(点击查看墨西哥各州政府近十年挖掘出来的无名乱葬场的地图)
离开的那天,两名腰挂手枪的格雷罗战士到访。我是港灿一名,见到挂在腰间的手枪呆左好一会,在小木屋中,我在背面看着他们的枪,看他们喝咖啡,然后听他们聊我听不明白的东西。其实我估计他们只不过是来串门子而己。这五天的宁静,是他们给的,是这个社区每个人,也是那些比他们更早的被杀害被失踪的所有格雷罗战士给的,但这些“战士”,只是在这片土地上,种粟米火芒果香蕉,养牛养鸡养猪的原住民,男或女,老或幼都要在必要时成为捍卫者。
据说在把政府和军队赶走的时候,整个丛林妇女小孩老人都参与,他们占领了警察局,把武器没收,把警察赶走,并驱走为警察和黑帮做事的居民。然后他们拿起枪和刀,每户一个 walkie talkie,紧密通信,任何陌生人进入丛林,他们便互报信息,妇女小孩会走到路上设路障,但一般他们都只会把陌生人赶走,并不伤人。他们建立自己的警察制度,自治全民会议及各式委员会。
这里很危险,这里很安全

这里,很危险,因为有一天军队或许会再驶进来。但这里很安全,房屋都不锁,电话手机电脑往屋里一放,从不担心不见。猪牛鸡,爱走多远走多远,没有人偷,也没有人捉。今天路过兴起采了邻居的芒果,明天经过跟他们打个招呼即可。出一次城,车沿途停泊十几次,social个不停,一个丛林很广阔,但人的距离却如此亲密。没有手机信号,约食饮或要探访便呼一呼 walkie talkie,永不用担心已读不回或拒接来电。他们说自治后,为防军队渗入,需要有社区居住的人介绍和带引,如果要进入丛林生活,就必需得到农民的充许。
那些人说这里危险,也有人说这些人危险。千百年来,刀和枪,是他们在丛林的生存工具,迫不得以,成为武器,需要时也要作战以护家园。他们没有从书本中学到什么是革命, 大部分人没怎么读过书,但他们从土地和生活中明白,什么是他们要捍卫的生活和价值。他们并不乱用武器,牺牲也可能是代价,但他们清楚他们要的是在丛林里自主自在地生活。
我地起义左廿年,等紧你地城市班友仔“革命”响应,一举赶走资本家建立大同世界,你地廿年都冇动静,得我地独撑,咩料?!
不用浪漫去想像他们,他们的力量没有强大到足以建立自己的国度,仍需要依仗着外界的社会制度而生存。当下他们和州政府的关系是既对抗又谈判,不充许政府人员、警察和军人进入,但会交税给政府,同时要求政府负责基建,亦需要得到政府给予的农民的各种认证制度,以令他们的农蓄产品可到市场出售。这个区算是平静的,据说另一些更激进的游击队在深山大林中,时不时会与军队起冲突。
有些人批评说,他们不是革命,他们没有把革命扩散到更大范围的目标,也没有革命图像,如何推翻整个制度。我不知道有或无,因为我只是作为一个废人去享受了几天宁静(手伤了连砖头也无法帮手搬),加上言语不通,大部分时间只可以对住人点头及不断微笑,看不出什么苗头来。不过,或者城市里的那些动不动就怕出游遇人身安全出问题的“革命者”,不防角色转换下,或者他们想着:屌你,我地起义左廿年,等紧你地城市班友仔“革命”响应,一举赶走资本家建立大同世界,你地廿年都冇动静,得我地独撑,咩料?!
这五天,友人给我的是人类学和历史课。
自小友人在美国,说着带格雷罗口音的西班牙文,再加上肤色偏黑,常被其他墨西哥人歧视,不承认她们是墨西哥人。友人母亲从不向她们述说家乡具体情况,及曾外祖母和祖母的故事,亲眼目睹家人被杀令她母亲无法述说过去。“我的国家总在战争中”,流放美国,及成为不被承认的人,这些成长经历使友人开始寻访自己的“身世”,不断努力挖掘自己家族的历史,挖掘墨西哥原住民的文化与历史。
在墨城初见友人,她以彩色围巾以包裹头发,煞是好看,我总是不自觉得地往她头上看,后来她说是在非洲学回来的。她一边画着她的画作,一边给我分享墨西哥原住民的文化和历史。她不像平常多见的喧闹夸张美式风格,表达清晰,但有种沉静。她是艺术家,也是人类学者,一人走遍十国,学习和了解原住民的文化,我只是隐隐然感受到她的情感与使命感,却不明白她那小宇宙的动力是什么。
她总喜欢带朋友回这个丛林,母亲曾问她不怕朋友见着这么简陃的木屋吗?她笑笑,然后再讲述她这几年来从亲友中收集回来母亲不能亲述的家族故事和原住民历史。
(小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