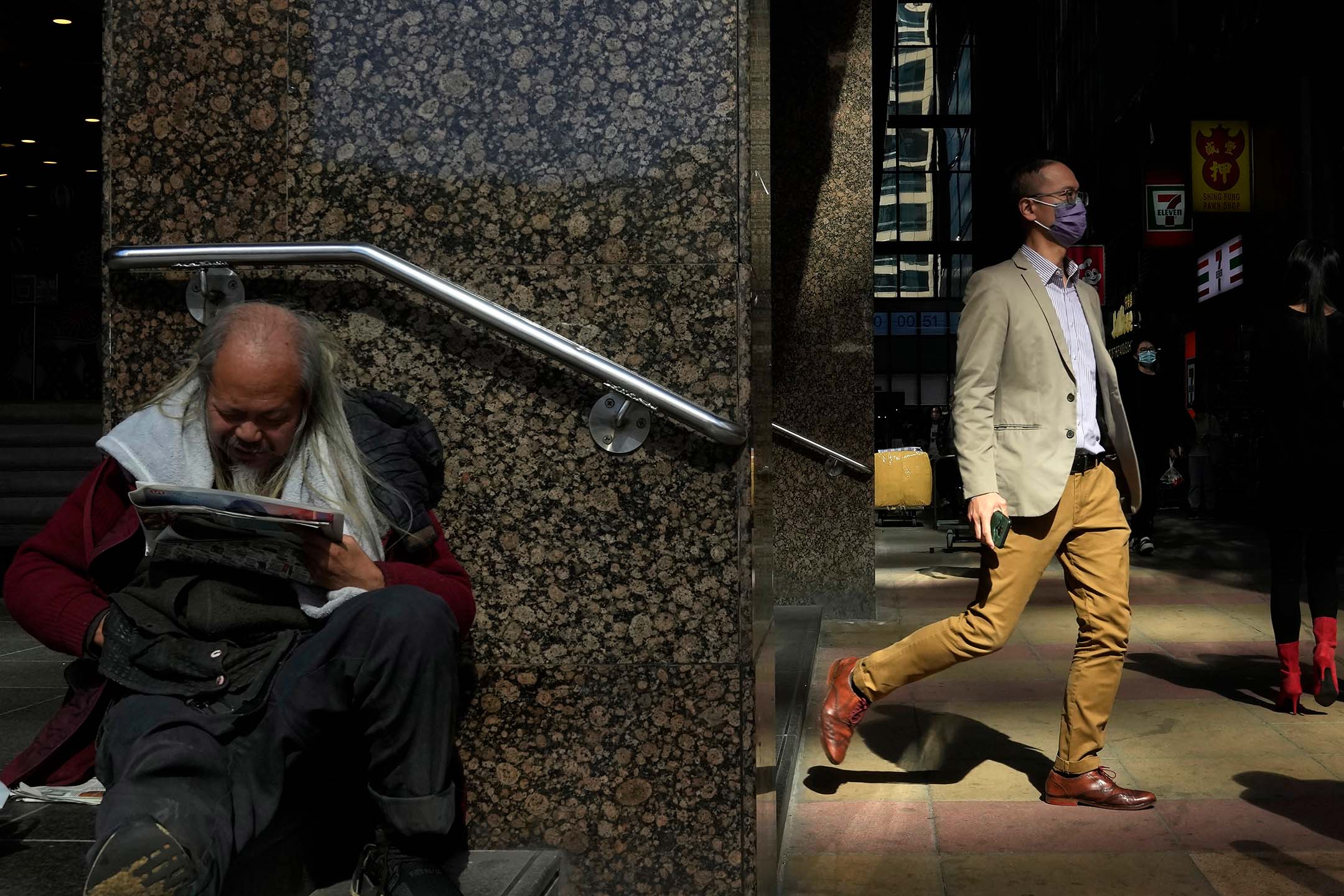我首先要为“香港文学馆”正名:它不应该是商品,不应该有所谓“专利”和“盗用”的问题。事实上,当香港作家联会(作联)会长潘耀明近日“忽然”宣布正式筹建“香港文学馆”,更是迅速地拟在明年4月开幕时,整个香港文学界均大为错愕、哗然,正说明了一个关于“香港文学馆”的历史现实:
“香港文学馆”由早不是一个抽象、空泛或言人人殊的概念,而是近十多年香港文学、香港文化乃至香港社会政治论述中,一个极为重要、丰沛且影响深远的论题,我们早就有大量跟“香港文学馆”相关的讨论,涉及香港文学价值、视野、文化意义、文学展示和推广的理念、实践方式和可行性等等,不胜枚举。但归根结底,却是一个关乎“文学公共性”的问题,而这亦是多年来倡议“香港文学馆”的过程中被讨论得最多、也说得最成熟的一脉。
本文不拟花笔墨重述有关论述脉络,笔者只想简单指出一个历史事实:在2009年因应香港西九文化区重启公众咨询而成立的“香港文学馆倡议小组”,才是有关于“香港文学馆”论述与倡议中,最具历史意义的起点。小组后来因西九管理局的冷待,而改组为“香港文学馆工作室”,继而成立“香港文学馆有限公司”,以“香港文学生活馆”的名义经营民间文学策展机构,至今一直是香港最具认受性的文学机构之一。“端传媒”于2016年的报导文章〈一场“无”中生“有”的文学抗争:香港文学生活馆的故事〉已有非常详尽的介络,亦在此不赘。
“香港文学生活馆”的多年实践,恰恰应合了整个“香港文学馆”论述的核心命题:文学具有公共性、文学应立足民间,而偏偏潘耀明所宣布要成立的所谓“香港文学馆”,却全然背弃了上述的历史脉络。
这当然不是潘耀明或“作联”“成功争取”的成果,而是经历三年多的政治洗清,政府跟亲建制分子已可以如取如携地控制公共资源,而无需经过舆论的监察和公共论述的检验。